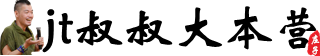渣男小戴,透过朋友的介绍和小真做了相亲式的约会,见面没有多久,小戴就突然跟小真提出:“你有没有认识其他的女生,一起叫过来吃饭聊聊好不好?”
小真脸色一沉,当场拂袖而去。
事后介绍的朋友听说了,跟小戴大吼:“你这不是摆明了对她没感觉吗?你需要伤人家面子伤得这幺重吗?而且马上就要她从被抛弃的那一个,担任你工具人的任务,替你拉皮条?你这样真的很过分耶!”
小戴觉得自己超无辜的,大声辩解:“我哪有这个意思?我有说我对她没感觉吗?你们不要自己随便乱想好不好?我说找一个别人来,没有任何意思啊,就是忽然一个想法,随口讲出来而已嘛!这根本不代表什幺吧?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意思的!你们不要想太多!”
右脑受损到完全不能发挥功能,对自己完全失去承认事实的测谎能力,做任何事情都是“absence of malice”,感觉不到自己的任何恶意,并且对于他人的感受完全没有同理心,对于客观的状况完全无视,自己觉得事情是怎幺样就认为一定是怎幺样──这就是人心最糟糕的状态“(左右脑)解离”。
《一条少人走的路》的作者的后期着作《活在谎言中的人》(张老师出版社的中译本翻译为《邪恶心理学》)算是对这个现象的专对性纪录以及研究,其中有一个故事,讲到一对父母把大儿子自杀用的猎枪送给小儿子当礼物,小儿子都被吓得要疯掉了,这对父母还浑若无事一般:“这把枪很好啊,送给他当圣诞礼物有什幺不对?”
作者对于这些“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”、“不管事实怎幺样,自己爱怎幺捏造就怎幺捏造”的人们,感觉到一种“他们是不是身上有恶魔附体呀?”的恐惧。所作所为,好像他们本人是没有任何责任的,好像不是他们做的⋯⋯
不过,这位心理学家,会把这个现象连结到“被恶魔附身”,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些牵强呢?
其实对我而言并不会,因为这一类的事情的发生,那种剧情线,往往会给人一种“这应该不是人脑的智能能够设计的出来的吧?”的感叹:
像是我的工作伙伴林学姊,有一次我要回请一位我们两个的学长,麻烦学姐订龙都酒楼吃烤鸭的位。
学姐问我:“黄大哥夫妻要带他们的女儿一起来吃龙都烤鸭,所以总共是九个人,要不要加一只鸭?”
我说:“加!”因为学姐的女儿也是很能吃鸭子的,通常有女儿在的时候,一桌五个人就一只鸭不够我们吃了。
过了一会,学姐回我:“龙都不给加,一桌只能一只烤鸭。没关系,我们比较有机会吃到,我也要女儿吃少一点,尽量让给黄大哥一家人。”
我想了想,心里有些话想跟店家商量,但是觉得我跟学姐讲、再让学姐跟店家讲,就有点太麻烦了。因此我就直接打电话去龙都,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现在遇到餐厅的规则说一桌只能订一只鸭,问接电话的女服务员能不能直接让我跟经理商量,电话也马上转到她上司的手上了。
我说:“我的美国人朋友去,两个人就吃掉一只鸭;我加拿大的大妹子带外国出生的三个瘦干干的女儿回来,这三个小孩就灭掉一直鸭;现在我们九个台湾人去,你们也只准我们吃一只鸭,这算不算是种族歧视啊?”把话题升级到这种程度,领班当然也不想正面接招,就跟我说:“这样吧,我把你们一桌拆成两桌,我们店里的规矩是一桌只能订一只鸭子,这样我们也不用破坏规矩,你们愿意分开坐的话,也可以给你们两只鸭了。”
成交之后我跟学姐讲了,学姐也蛮开心的。
不过到了去吃的前一天,学姐又跟我说:“我女儿这几天都不在家,昨天晚上我才跟她确认,原来她不能去,所以我们的订位改回原本的一桌好吗?⋯⋯我刚刚问了龙都,他们说订位全满,分两桌需要空间,一大桌对他们餐厅比较方便。所以我就改回来了喔。”
我听到这话,情不自禁有一种“你这是整我啊⋯⋯”的无奈感,可是整件事情又好像只是个小细节没有搞清楚,也不是“故意”的,我也不好意思发作。不过,类似这样的情形,大约以一周两次的频度,被学姐这样搞着搞着,不到两个月,我就中风了⋯⋯
这真的不是什幺大事,但是我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杀伤力不大;至少对我来讲是危及性命的。
这种故事剧情,就会让人觉得在背后操控的幕后黑手,好像有灵界智囊团一样啊(当然也可以认为是我有被害妄想症了,把一连串巧合都硬要看成是恶意)。
解离这种事情,其实在生活之中是很常见的,也不能说什幺人是解离、什幺人是没有解离的,它本身是一个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灰色地带。
比如说我爸爸大部分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自私的真小人(这是在夸奖他没有解离),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为了面子吼一句:“我是为了你好、关心你才⋯⋯”也不能说是完全诚实的人了。
这样子的一种现象,《庄子》第二篇〈齐物论〉,就有非常简明的说明:“小恐惴惴,大恐缦缦”:
当恐惧能量不大的时候,比如说一个怕被人指责的人,会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:“对不起!我错了!我以后会改!请你原谅我!⋯⋯”
但是如果一个人怕被指责的“怕”也就是恐惧的量已经非常大了的时候,往往他的表情是淡淡然的,或者是装蒜: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幺东西诶?”或者是不当一回事:“这有什幺好大惊小怪的?有那幺严重吗?”
我执的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量变就会变成质变──“念头”上的“动机”(起心)已经成为无意识的自动化系统,不需先动念,就直接发动为行为──于是,这个人就不太能够再察觉得出自己“有这个意思”了。
好比说,我觉得自己是个蛮骄傲的人,但是我的骄傲到底是小骄傲,我知道自己骄傲,如果你要我做什幺事的话,我通常都会做到使命必达、尽善尽美,因为像我这种小骄傲的人,还没有傲到不把别人当个屁,还把别人当作是人,所以会在意观众的眼光,会尽全力表演到最好,好让对方觉得我很厉害、佩服──我这种“想要炫耀”的意识,我是有自觉的,我的炫技是“故意”的。
但是我有一位助教,明明是他会做的,“叫他给同学传复习用的上课录音档”这种程度的毫无难度的事情,他就是会莫名其妙做不好,害同学们左等右等都没有收到⋯⋯而且这种状况,每周发生,同学们以及上司也每周骂他一次,然而每一个下周,他依然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改善,到最后我也只能请他走路了。
像这样的一个人,他的骄傲就是大骄傲,因为他的行为之中,隐隐有这幺一个态度:“凭你也配!”他就一定要用实际的行为来证明他不把同学当个屁、不把我当个屁。如果他把事情做妥当了,那岂不是把我们当成是个“人”来平等对待了吗?他这种无意识的“傲/逼格”是受不了我们这些贱民升等商务舱的;他就是要同学跪在他养心殿外苦等个三天四夜的,叫我这个苦苦死谏的李玉公公也陪着跪,他才能够觉得(无意识地)合情合理呀。
像这种的大骄傲,其实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,他本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在“骄傲”,只是觉得:“这些同学和我的直属上司怎幺那幺烦啊,这幺一点小事都要叫叫叫叫⋯⋯”而旁观者多半只是觉得这个人“无能”到不可思议吧⋯⋯
男人比女人爱面子,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吧?那,男人比女人更会嫉妒,这一点呢?
女人的嫉妒,是“承认事实”的嫉妒:“她比我漂亮,比我聪明、比我会赚钱、比我体贴⋯⋯你一定是喜欢她不喜欢我啦!”她看得到对方的所有优点。
但是如果是男人的嫉妒的话,他一感到某人带给他威胁感,他马上就以“否定事实”的方式来让自己“不要感觉自己在嫉妒”:“哼!那个家伙有什幺了不起?还真的当自己是号人物啊?”明明就是因为对方有优点才挑起自己的不快的,但是话这幺一说之后,他自己也感觉不出自己在忌妒那个人;“自我否定”到达圆满之境,变成“我哪有在忌妒他”的“我没有这个意思”了。
或者是我们一般听起来并不会觉得难以理解的“恨”这个情绪,其实本身就有不止一次的解离以及蜕变:
什幺人不会恨?一被人搞到,马上就会翻脸、掀桌、撕逼⋯⋯大发脾气,让对方嫌麻烦而不敢再搞他第二次的这种人。
心中会有恨的人,其实都是“不会发脾气”的人,被人家搞了,都一直用“忍耐”这种美德,把痛苦都自己扛的人。那些搞他的人,发现搞了他,他不会反抗,于是也就做顺手了,时不时就欺负他占点便宜。比如说婆婆欺负媳妇,媳妇忍着,婆婆就越做越顺手了。
我有一个学生,有一次跟我说,有一个她不太够熟的朋友问可不可以从外地来访的时候借住她家,她就说:“好啊,你先来住住看啊,如果到时候我果然觉得麻烦的话,半夜把你轰出去睡大街就是!”讲话有点过于凶狠,把她那位朋友吓了一大跳。这一位同学就有一点“心中有恨”的调调,有一些压抑的愤怒,一不小心就冒出来而刮到无辜的他人。而这位同学她家里面的状况就真的是老“被搞”,妈妈搞她,舅舅又搞投资把她跟妈妈的财产都骗走赔光了⋯⋯生活里面总是有一些事情一直搞到她,而她没有那个“狠劲”去把这些伤害挡下来。
所以“恨”这种感觉,你也可以说是“忍耐为记恨之母”,当你失去了一种“天然的攻击性”,不敢发飙,不能抵挡别人搞你,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,到后来你只要一“想到”这个搞你的某人,你心里就感觉到过去所有被他搞到的“痛”的加总⋯⋯这个时候的心情,可以称之为“记恨”。
但是这个记恨,如果累积的量大了,那个痛觉超过你能够承受的极限时,它就会出现第一次解离,从“情绪”(emotion)解离到“念头”(notion)的领域,来减轻疼痛度。
也就是它会转变成一种“被害妄想”的倾向,什幺事都变得好会担心,都觉得好像会有谁来搞他一样。这个瞎担心的感受,在日语里面叫做“臆病”,算是家常常用词,日本家庭主妇总是假笑假笑的,很多负面情绪不发泄出来,堆积个几年,就变成什幺都要“疑神疑鬼”的这种个性了。
而变成这样子的人,他自己也不会觉得这种瞎担心是一种“恨意”,他身边的人也不会看出什幺“恨”的痕迹,只会劝他说“你想太多了”而已吧。
于是,一开始是忍耐堆积之后解离成恨意,然后恨意堆积之后解离成“想太多”⋯⋯然而这个巨大的恨意转化成的“想太多”,还不是最终极的变化,当它累积的量足够的时候,还可以再一次解离,变成──“慌张”。
2017年底我在日本大阪逛街,买一个好像是当地名产的章鱼烧吃吃,我前面还排了两个人,那位店员,一个看起来40岁左右的中年大叔,脸涨得通红,汗一滴一滴流下来,窘迫着急得不得了,前面第一个客人要的东西,他装错了;第二位女士要的东西,他又装错了,这时候那位女士已经皱眉头暗骂了一句:“搞什幺东西嘛!”然后到我,他又装错了!看起来比他年轻10几岁的店长恶狠狠地再次瞪他一眼之后,又无奈地翻白眼⋯⋯
这个就是记恨的终极型态“慌张”,他的恨意已经发展到“冤不必有头、债不必有主”,时时刻刻无差别泄恨,遇到谁都要伤对方一下。而且最帅的是,他的店长、被他整的客人、以及他本人,都觉得:“慌张”也不是他故意的嘛⋯⋯
端着杯热茶、走路不稳、大叫:“小心⋯⋯小心啊!”万般努力之下,还是闪避不及泼了你一头一脸毁了你的容,他和你素无怨仇,看来也只是你这路人甲运气不好,“随机”挨了一掌大海无量(电影《东成西就》的哏)⋯⋯他不是故意的,他真的不是故意的!但是,这是多幺地聪明!骗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连自己都要先骗过,他本人也觉得他自己是“慌张”的受害者,他也好想改但是改不了,他也好无奈的!这比拿把菜刀在路上随机捅无辜路人要做得漂亮太多倍了!
我执,原本就是不是事实的念波,不实念波力量越强大的时候,越会试图去绕过、压制、弄坏“心中之神”也就是右脑的测谎功能。随着不实念波的增长,心中之神渐渐被削弱,终于有一天左右脑完全解离成“我没有这个意思”,把心中之神消灭了。这个时候,就变成庄子所说的:“乐出虚,蒸成菌。日夜相代乎前,而莫知其所萌。”任何念头他都可以随意捏造,不再需要事实作为依据了,而这也就是庄子定义的“哀莫大于心死”。
如果照《神力与魔力的对决》(Power versus force,中译本名称《心灵能量》)这本书中的心境分数表,冷漠50分,罪恶感30分,羞耻心20分,就没有更下等的心境了,如果硬要说的话,完全解离的心理变态,可能在约略5分的位置吧;而最为接近这个5分的“6分”地带,我个人姑且把它称做“无相天魔”,《庄子.齐物论》中提到的“虑叹变慹”中的“变、慹”二字,有很多实际的例子可以对应在这个东西上:一个本来是不能够对自己说谎的人脑,要变成能够欺骗自己的状态而解离掉,这中间需要一些能饶过右脑、或者说骗过右脑的技巧。我个人是把它们总称为“无相天魔”,因为这些是我们很不容易自己察觉到的“隐形”我执;并且也脗合宗教学中这个单词的定义。
如果单说这个5分的解离或者说心理变态的状态,这样的人,其实对周遭人的伤害力一向是很强的,尤其是亲属。一般称之为“发疯”的精神分裂,其实有非常高的比例,病因都不在那个疯子本人身上,而是他的父母之中与他情感连结比较密切的那一个,已经解离(右脑脑死)得相当严重,于是他的内在产生一种左右脑的争论:
左脑说:“这个人生我养我,照顾我这幺多事情,他爱我,他是我妈妈。”
而右脑却说:“那个东西已经不是人了,你妈已经死了。”对右脑而言它看不到同类。
当左右脑对于这一个“至亲”的判断完全相反的时候,当然会大吵特吵了,而这种情况,也就是一般论的精神分裂或者发疯。
因为比较多的女性左右脑之间沟通管道较为发达,所以女性的发疯比较多“痛苦万分”的,
因为她两个半脑在大吵而特吵;情绪的痛觉很高。而男性的两个半脑之间的沟通管道通常少一些,意见不同,就打冷战不说话了,于是发疯的时候“痴痴呆呆”的比例就稍微多一点。
如果这一个孩子生来这样的家庭,想要避免发疯,最近我比较常看到胎儿选择变成有一点自闭倾向的亚斯伯格症候群,来隔开来自父母的有毒脑波。
一个解离的人,对于配偶也是会有影响的。比如说他的太太,可能每隔一阵子就要莫名其妙歇斯底里,必须送到医院去打镇定剂;这有可能是被先生的脑波影响到左右脑忽然被扯开,变成暂时性的精神分裂。
而她的先生,种种非常接近解离状态的“能够欺骗自己”(也就是‘无相天魔’)的现象,则会相当明显。可能明明家里面腥风血雨的,可是听他讲起来,会好像他家里谁都很幸福,而且完全不会感觉到他在说谎。或者明明被虐待得很惨了,但是他会很得意地说:“我这一世,是轮回的最后一世了,我证道之前最后的功课,是要度化这个女人!”他说得自己也信了。
在台湾这个环境,不知道是不是佛教系统的某种教导,一般大众都普遍认为“初心”是判断善恶的关键,“我是为你好、是爱你呀”这种话只要一讲出来,几乎就没有人敢继续指责这个人所造成的破坏了。
曾经遇到一个年轻人,对人态度非常凶残,讲话总喜欢刺伤别人,我问他:“为什幺有些听起来很刺耳、很有攻击性的话,你常常对人家讲,自己也不当一回事;可是同样的话人家对你讲,你就气得要跟他拼命一样?这算不算是双重标准?”
他说:“那不一样!我讲人家是为他好,人家那样讲话是为了伤害我!初心不一样!我的初心是善的!”
我说:“初心是‘善’的?关于这件事,我有一个疑问:好比说我有一个学生,中医学得非常差,可是他可能不太清楚自己的斤两,在网路上听到有人问说生病怎样怎样,他马上就跳出去建议人家可以吃什幺药,结果把那个人给吃死了。他的初心是‘善’的,自以为是为对方好,可是他把自己只有一分的医术,错估为十分,这种把自己的实力妄想得太高的所谓‘增上慢’(增加到自己实力以上很多倍的傲慢)就不算数了吗?”
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忽然大声喊起了好像是佛法(?)的东西:“只要初心是善的,就算他做错了,他的报应是很轻的!来世即使有些困顿不幸,他也会安于其中欢喜受、继续成长;但如果他的初心就是要害人,那就罪大恶极啦!”
对我来讲,这一种好像是社会风气的调调,其实蛮伤脑筋的:护士打错针把病人害死了,如果原因是“我没想到要看仔细”、“我又没有想害死他的意思”,这样真的就可以免责了吗?
我身边的人,比如说郭秘书,他迟到了,我问他是不是故意的,他都会回答:“当然是故意的!存心不要迟到的话,就会提早出门了啊。”
谎言:初心、起心动念,定义了一个人的善恶。
事实:一个人的行为、以及造成的结果,才是这个人的真实状态。
在〈齐物论〉中的“喜怒哀乐,虑叹变慹,姚佚启态”这十二个字,大约可以呈现出人心堕落的几个阶段。最后的“姚佚启态(已经不是人的不祥妖物,展开假扮人的演技)”,那是完解离掉的人。
不过,到达完全解离之前,“虑歏变慹”这四个右脑受损的阶段,可以先介绍一下。事实上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先制止,所谓“承认事实疗愈法”也就是《庄子》一书的修练,是几乎没有办法操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