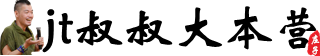果且有成与亏乎哉?果且无成与亏乎哉?我们这个世界,因为没有了道,所以有了爱与美。所以庄子说,到底哪边比较好?好像也是『都可以』的状态。只是我们要认识到,我们得到了爱跟美,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体感。
有成与亏,故昭氏之鼓琴也;无成与亏,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失去了道,我们就有了伟大的艺术作品,有了伟大的学术和哲学的沉思、 哲学家代表惠子倚树沉思。没有道的世界,就有了美好的东西;有了道的世界, 音乐家也不用弹琴了。所以,到底哪边比较好?庄子说:我也搞不清楚。
现在也有学者说:这一期的人类,是大约四千年前,头脑才脱离混沌(进入
『二分心』的状态),开始学会使用左脑的。学会使用左脑之后,人类的科技文明,才飞速地发展起来。而欧洲从五世纪到十几十几的文艺复兴之间的所谓
『黑暗时代』,欧洲人还一度掉回过右脑主导的混沌之中,缺乏个体性,全凭宗教的『神谕』活着;当然,这段时光,以科技文明而言,就是发展停滞不前的黑暗时期了。
想想我今天有电视可看,有捷运可搭……我还真不敢大叫:『大家来实践《庄子》!』啊。我也需要左脑系的人,帮我造出好用的新产品嘛。
可是,这几个音乐家啊——到这里,庄子的文笔就开始让后代的读者有点混乱:庄子到底是要写这几个音乐家、还是要写他的朋友惠子?我觉得庄子好像比较想写惠子——昭文之鼓琴也,师旷之枝策也,惠子之据梧叶,三子之知机乎!这些人的头脑都是非常好的。皆其盛也,故载之末年。所以,他们的学术成就什么的,就会被写在书上,『载之末年』,流传下去。
可是,这种思想流传后世的伟人,比如说庄子的朋友惠子好了——庄子在讨论惠子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——他对惠子的第一个质疑是:唯其好之也,以异 于彼,其好之也,欲以明之彼。非所明而明之,故以坚白之昧终。惠子这个人, 他喜欢这些东西,是因为这些东西让他显得跟别人不一样。可是,当这个人喜 欢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,他要人家懂他,就很难了。
人妖伟大,就必须跟别人有不同之处。惠子是一个希望别人崇拜他的人。既然要别人崇拜他,就必须是『我会,你不会;我懂,你不懂』,不然你怎么能 崇拜嘛?可是惠子会了一些别人不会、不懂的东西之后,他又落入另外一个矛 盾:『我的东西你都不懂,你不知道我厉害在哪里,你怎么有办法崇拜我呢?』
那你到底是想要别人懂、还是别人不懂?
庄子说,惠子就卡死在这个『坚白之昧』里面。
我们先还不提那个『坚白之昧』、我觉得庄子形容惠子的这个状况,我们每一个教书的老师都会面临到类似的难题——你到底是要崇拜者还是理解者?你只能选一个。理解你的人不会崇拜你,崇拜你的人不会理解你。
象是我身边的朋友对我还蛮熟、蛮理解的,可是,我一个台湾朋友阿信,有一次看到我跟郭秘书、天威助教吃饭,他就说:『好奇怪啊,你的助教跟秘书不是应该叫你老师吗?为什么他们都只叫你杰中?』我就想,我们从前就是老朋友了,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叫的;不过话又说回来了,我的所有助教,什么丁助教、小方助教,都是叫我杰中,也没有叫过老师啊。
莹莹叫我叔叔,是因为我从前跟她妈妈交情很好,差点做了她继父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我后来讲出来,台湾有个女同学就再也不敢叫我叔叔,有莹莹个人的理由;但是别人叫我叔叔,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做了二十年,我写东西的署名、同时叫我,都是用我的英文名 Jon Tan 的缩写JT。差不多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, 二十出头的新进同事都叫我 JT『叔叔』。后来我弄个博客,也因为我在出版社写过一些卡通歌曲翻译跟赏析的稿子,出版社说不能出书,因为日文歌词会有 版权争议,我想那就算了,就随便坐个博客贴一贴,贴着贴着,又写了一些关 于中医的东西,然后就莫名其妙地爆红。『JT 叔叔』这个称呼是这样来的。一开始署名是出版社同事这么叫我,后来就觉得:学生叫我叔叔,就不叫我老师 了,也挺好的。
2019 年 8 月 5 日星期一
我们做老师的都会面临『我到底要崇拜者还是理解者』的问题。而我也真的看过,我的同业卡在这个麻烦的地方;他真的很讨厌他会的东西别人也会;可是当他的学生不会的时候,他又愤恨地指责学生辜负他的教诲。
我们一般人都认为,学问的正道是师徒的传承。可是实际上,如果你对武林掌故有一点涉猎的话,就会知道武林中人,那些做师父的其实很怕学生赢过他, 或多或少会藏私,甚至前阵子有部电影叫做《道士下山》,一个师父因为徒儿 功夫好,所以想尽办法把他弄死。其实在一个师门的系统里,如果这个师父, 在心底终究有一种害怕;害怕他会的,徒儿也会。那徒儿的日子怎么过啊?徒 儿在这个结构里,就足以被虐死了。
我的情况是这样子:因为我的目标是教书,不是我中医要比你好,也不是我
《庄子》要练得比你好。我的目标是我教书要教得比别人好,所以我的学生, 中医学会了,甚至学的比我好了,我并不在乎,因为那不是我关切的东西。
不过,虽然我一直以为我教中医是很大方的,我不怕学生学得比我好,可是真的到去年十二月的九日冲刺班,有个很年轻的小叶大夫从加拿大来上我的课,那时真让我觉得;那个小孩子的医术比我好。那时候我教书,情不自禁地会有一种难堪、不安的感觉;说自己不在乎,其实是太超然了。还是……会有一点怕的啦。
有老朋友曾经问过我:『你说你不在乎别人医术赢你,那如果有一天有人真的连教书都教得比你好,你会怎样?』
我的确看过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力胜过我的人。我说:『我会气得大哭一场, 然后,爱-上-他。』我确实有过这样的经验,大概在这件事情上,暂且可以这样释怀;还不至于跟惠子一样,陷入『你不可以会,又不可以不会』的误解循环里。
庄子这句话,真的能让我同理到,这个世界上,在很多很多师门之中,在很多很多恩师教主之下的徒儿们,是活得有多么地痛苦!
因为我是教书者这一方,我们这些教书匠,固然时不时会聚在一起说说学生坏话,说什么『这个学生哦,教他多少次,点他的时候他一定装傻』,或者『这个学生教他多少年,还不是一脸横肉』之类之类。我们固然会这样来找学生的茬儿,但其实,我们也对整个师徒之间的关系有某种熟悉。
所以,我可以理解,站在老师的一方,当我不是真心想要把学生教会的时候, 就会产生这种矛盾——你不可以不会,也不可以也会——也是,作为老师,自 然而然就会无意识地形成一种行为,就是:把话讲得很玄!你不一定清楚意识 到自己害怕学生赢过你,但其实你是有害怕的。比如有的老师会说:『哎呀, 你们尽管学,我可不怕你学成我的本事啊!』说这个话时,心里面好像还是微 微颤抖那一下,似乎不是真的不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