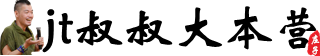如果至人的存在,其实是我们这个狭小的地球世界之外的话,连死跟生都无所谓啊。死生就是穿一件叫做肉体的衣服在那边玩一下——台湾叫布袋戏,你们叫什么?——活着不就是手伸进那个布袋戏的人偶去扮演一个角色,死了就是脱下这个人偶。对他来讲,不管是死还是活,我都还是我,你问他这个三次元的世界,什么是利、什么是害?什么是好的、什么是不好的?这种事他能晓得吗?
如果跳到最后第七篇的开头来看,这好像是王倪把他徒儿啮缺震醒的一个对话。从这个对话里面,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心做一个不一样的设定——从前我们被教导的东西是:你『不知道』就是不好、就是无能、就是笨蛋;但是我们学了《庄子》,我们就要重新对自己做一个新的设定;正是因为我有感知力、我聪明,所以我不轻易地认为我知道。
『不知道』才是聪明人会有的态度,象是我们台湾的老同学琬惠姐就感慨过
——因为她是西医界做血癌数据的相关工作人员,琬惠姐很崇拜西医血癌研究的某教授——她就说:『你看到那位真正了不起的高手、全华人治血癌的第一人,你就会知道,高手绝不会轻易觉得『我知道』。如果有人问他一个问题, 他就会反问再反问,绝不轻率地给出答案。如果有人要求他做出一个轻率的回答的话,他就会说:『你现在给我的种种 fact(事实)都还不够,这个病人的很多情报都还没有收集到,我不能够随便做出结论,对不起。』
真正的高手,就是没有在一切情报都确认再确认以前,不轻易地觉得自己『知道』的人;反过来说,在我们那个中医买药看病的群里面,看到的状况,就完全是另一种光景;我的那些不肖中医学生,基本上就是《名侦探柯南》里面的毛利小五郎叔叔状态:随便有一点点线索,根本我们这些老手都觉得还不足以下判断,他就可以说『凶手就是你啦』!所以,真正愚昧的人,就是那种什么都轻易觉得自己知道的人。
像我看一个病人,都是差不多一个病人要看两个钟头,能问仔细一点,就是要问仔细一点。那么轻易地就可以做出决定,那时他太『无知』才会觉得他知道。
而且这事本身就是一种解离啊:你没有把人医死的意思,可是事实上你招招都是在要他的命。中医爱好者,要用无知(西谚有云:所有的无知,都是故意的)灭尽心中之神,很快的嘛。
如果知识比较丰富一点,知道一件事情还有很多可能性的时候,我们在情报收集完全以前,不会那么轻率地结论的。
如果你真的要练《庄子》的话,就老老实实地承认『不知道』,而且安于这个不知道,这才是前面一节《庄子》说的『省能源』(葆光)的基本心理姿态。
2019 年 8 月 30 日星期五
既使我与若辩矣,若胜我,我不若胜,若果是也?我果非也邪?我胜若,若不吾胜,我果是也?而果非也邪?其或是也?其或非也邪?其俱是也?其俱非也邪?我与若不能相知也。则人固受其黮闇[dàn àn;黑暗、没有光],吾谁使正之?使同乎若者正之,既与若同矣,恶能正之?使同乎我者正之,既同乎我矣,恶能正之?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,既异乎我与若矣,恶能正之?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,既同乎我与若矣,恶能正之?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,而待彼也邪?"
"何谓和之以天倪?"曰:"是不是,然不然。是若果是也,则是之异乎不是也 亦无辩;然若果然也,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。化声之相待,若其不相待。和之以天倪,因之以曼衍,所以穷年也。忘年忘义,振于无竟,故寓诸无竟。"
我过去这些年教《庄子》,现在回想起来,都觉得蛮对不起这一段文字的。因为过去我总觉得,这段文字讲的内容,谁不晓得呢?像废话一样。所以也没真的很花心思去教,就随便念过去。
这次再读到这段文字,我才发现,这些事情,虽然是很基本、很简单、甚至并不需要谁来讲解你也会明白的事实。可是,真的能承认这个事实,其实还是很要紧的。过去以为庄子在说废话的这一段,现在重新再看的时候,对于它实践上的价值,我感觉就蛮不一样了。
他说:我跟你两个意见不合吵架了,如果你赢了我、我赢不了你,你就果然是对的,我就果然是错的吗?如果是我赢你、你赢不了我的话,我就一定是对的,你就一定是错的吗?还是有可能,我们谁有可能是错的,或者说两个人都是错的,还是两个人都是对的?
无论这个可能性是如何的排列组合,重点是:辩论中的两个人——我跟你—
—是没有办法判断的。
『没有办法判断』的这件事,记得我二十三岁的时候,曾经有一次跟一个外国朋友,辩论一个类似政治方面的议题,那个时候讲着讲着我也烦了,就跟那个朋友说:『嘿,老兄啊!我们两个之所以辩得起来,就是因为你也没有能力知道完全的真相,我也没有能力知道完全的真相,所以才能吵,对不对?我们在这个时候,就承认我们两个都不知道真相好不好?这样就不用再吵下去了。』如果某一方拥有百分之百的事实的话,根本是没有可辩论的空间的。
可是,当我们都没有事实,还用力强调自己的正确性,则人固受其黮闇[dàn àn],这种意见就会把另外无辜的人都染黑了。我们人也是很可怕,不管吵输吵赢,都还是会想要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,所以我们的意见流出来就会污染到别人。
这样子的话,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好像是『裁判』的角色,来告诉我们,到底吵架的我跟你,谁是对的。可是庄子就说:这时候你去找一个当裁判的人的话,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?如果这个裁判是认同你的,说你是对的,问题是我都已经觉得你不对了,再多一个跟你同一国的人在我面前,我就会服了吗? 不然找一个跟我同一国的来当裁判好了,跟我是同一国的,你会服吗?这样的人能当裁判吗?不然找一个也认同你,也认同我的人来当裁判了,他如何能说我们两个谁是对的?如果再找一个,也不认同你、也不认同我的人当裁判呢, 既然我跟你都要吵了,那个人跟我们两个意见都不同的话,我们一起跟他吵是不是?
这些所有身为一个裁判的qualification,他做为裁判『资格』的可能性,在这个时间的本质上就已经被否定了;找裁判也是没有意义的。
这样的一连串的对话,当然我想同学可以理解,庄子是在反复说一个很单纯的事实;裁判这种东西,其实在事件的结构本身,就已经决定了『它是没有意义的东西』。可是问题是:现在的我们,还是会『希望别人相信我』。当然这个『希望别人相信我』,讲到它的基盘,依然是我执作祟。